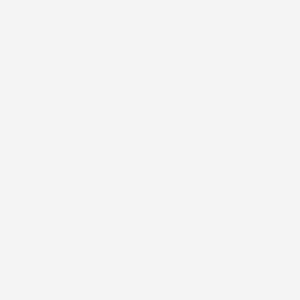
《路从今夜白》李思燃
南方街巷的雨水霏霏,云烟蒙蒙,花枝隐隐与北国一路雪飘的风光区别甚异,见惯了江南的揽风招雨,却未曾识过东北的大雪三尺。
我想,父亲也未曾见过吧。
是拂晓,冬日的天黑透了,没有一点想冲破黑暗的意思。我在被窝里半梦半醒着,依稀听见房间外窸窣开火做饭的声音。“真的很讨厌,大清早地又开始烦人了。”我捂紧被子,两腿狠狠地砸在床上。
听见我这边有动静,父亲轻手轻脚地走过来,悄悄地把我的房门关起来,又轻手轻脚地走回厨房。我格外讨厌父亲那种胆战心惊与小心翼翼,他越是这样,我越是想激怒他。可他总是处变不惊,唯命是从。
突然我的床边传来一个声音:“下雪了!女儿快起来看......真的是雪!”父亲的声音藏不住激动与欣喜。我第一反应是从床上跳起来,立马冲出去看雪。鬼使神差地,我嘶哑着吼他:“喊什么?没看见我在睡觉?”天边初晓的光照进房中,恍惚间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烁的明亮黯淡下去。他掩起我的房门,蹑手蹑脚地退了回去。
听到脚步声消失在黎明里,我冲出去,来不及披上外衣,冲到那条被积雪淹没的路上去。
是雪!真的是雪!一夜之间,原先被青苔覆满的路上淀起了皑皑白雪。
小路上找不到落脚之处。朦朦胧胧的亮里,笼上一层微蓝的萤火。空气里弥漫着冰冻的气息。近处那棵落光了绿叶的树杈上又盛开了雾霭的痕迹。有晨风拂过,我清晰地看见了空气中漂浮的水汽向光亮的地方扑去。
寒气猛地袭来,我打了一个哆嗦。背后一个更冷的声音响起:“不冷吗?回去穿衣服去。”我一惊,眼里闪过一丝慌乱,却漫不经心地答到:“下这么大的雪,路上都是,怎么出去?”我强装镇定,底气弱了些许。说完便逃离父亲的眼神。帽子围巾手套耳罩棉裤羽绒服,被我不遗余力地往身上套。再次出房间,天已经大亮。外面时不时传来人们的惊呼。我穿过堂厅去桌前吃早饭。不经意地朝外面一瞥,这惊鸿一瞥猛地刺痛了我的眼。父亲光溜着双手,紧握扫帚,穿着那双掉了底子的拖鞋,在积满雪的路上佝着腰。
他在扫雪!
只是我刚才胡编乱造了一个糊弄他的借口,父亲居然当真了!我看见他头皮上沾了片片雪花,分不清那两鬓间斑白的是发还是雪。他就这样低着头佝着腰,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,挥舞着扫帚......雪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,它打着旋儿不停地往下坠。我像是慌了神,想去接住那可恶的白衣魔鬼,也想喊父亲停下,快停下......
从房间到餐厅的距离不过十几米,我好像是走了很久,走了一个青春?把父亲的脸走出了岁月的印记?
“刷—刷”扫帚与积雪摩擦的声音越来越远。小路上隐隐有青石板的影了。我突然害怕起来,那声音可不要随那洁白的雪花一起飞了去...我冲出去,积满雪的小路上有了能容得下双脚的一席之地。我喊着:“爸!爸!屋里的菜凉了,快,快去热热!”他往我这边看了一眼,眼里的欣喜似能融化那漫天白雪。“好!爸这就来!”
那一截才干净些的小径又铺上了层层冰花。雪花放慢了脚步。我赶紧拾起扫帚,把能剩下小半截路上的雪扫净。我的眼里突然滚落了什么东西,分不清是因为雪飘进眼里还有因为别的什么...
太阳终于在傍晚十分露了脸。我拉着父亲说想出去看雪融化的样子。走在那条湿漉漉的路上,灌木丛顶着残雪,泥土上零星半点吐着泡泡的融雪。还有天边那颗金黄的火球,不自觉地拉紧父亲的手。
夕阳西下,我们的影子映在石板小路上,映在这条朝夕相处的路上。
路从今夜白,也从今夜明了。
